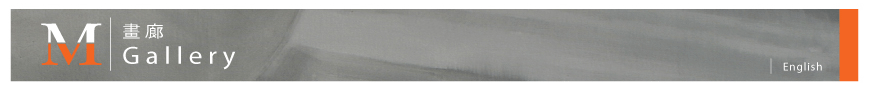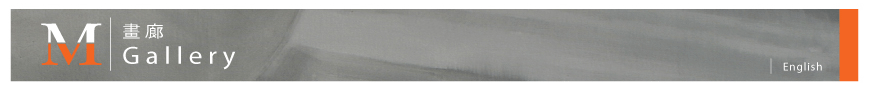如果我的作品有个倾向性的东西我会很警惕,我对暧昧性与不确定性很感兴趣,这种状态是非曲直很灰色的,并且这种读解可以产生新的关系,……不确定本身 就是控制,它限制你把作品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倾向性。……既放弃自恋的、胸有成竹的、置信不疑的、准确无疑的思想方式,而将质疑作为艺术工作的起点。……艺术不再是终极瞬间的狂迷和艺术家以此作为自己权力的喜悦。——汪建伟
汪建伟从20世纪90年代起,艺术创作开始从架上绘画转向了观念艺术。他创作的领域从媒介和手法上涉及装置、录像、照片、雕塑、记录片、表演、戏剧等。1997年,他的作品《生产》参加了由卡特琳娜·戴维(Catherine David)策划的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这也是大陆艺术家第一次参加此展览。
文本的历史与历史的文本
4月1号北京酒厂艺术区的阿拉里奥(Arario)画廊2号展厅举办了多媒介艺术家汪建伟的个展《飞鸟不动》。展览的标题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enon)的假定,即“如果时间只是由瞬间碎片组成的话,那么飞着的鸟就是静止的”。作品中另一个重要的背景素材来自于中国的“连环画”故事《双龙 会》。汪建伟认为历史可以分成历史的文本与文本的历史,可以被反复从某一处描述,也可以同时被理解为不断中断的片刻。作品以长约6分30秒的录象、8张照 片、一组雕塑这三种不同介质构成,呈现出一种静止影像与连续影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之间也能产生新的互动,它被汪建伟称为灰色关系地带。“飞鸟不动”这 个概念要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放在一起,它才成立,是动态关系里的一个静止影像,这如一把剑在挥动时,每个经过的空间都会有把剑,但静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 却只有一把剑。
对于文本的解读,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如汪建伟20分钟的《剧场》影像作品,它来源于白毛女的故事,分为歌剧、电影、芭蕾舞等四个部分,最早根据民间 传说,艺术家把找得到素材的综合起来,找不到的重新演。观看的人由于是不同时间进入放映的场,他们得到的信息完全不一样。在这里艺术家并没有提供一个影像 的阅读方式,Video的阅读其实是有空间的。阿根廷的赫尔博斯(Jorge Luis Borges)的小说里也有这种大量的时空错乱,他认为对于时间我们不可能改变,但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时间。
社会化平台上的影像收集者
汪建伟对社会各种不同关系之间的文本很感兴趣,可以说他是一位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统筹型的社会学艺术家,并能够以系统的方法论来引导观念的宏观实施。 从影像媒介与技术的角度来看,汪建伟认为自己更象是个影像收集者而非纪录片工作者,因为纪录手段方法包括提问与跟踪,但他不想介入对方任何东西。他把某种 视觉要求和技术绑在一起做的社会学调查,这种调查使线性方式的“工作室”概念消失了,他觉得自己更像影像行动者。对于影像的另一个观点是汪建伟认为比尔· 维奥拉(BillViola)所建立的这种简单重复的录像模式其它与我们的关系不大,而平常看到的电影建立的历史观却是我们集体主义很重要的历史观。如他 2002年在长征的作品《中间地带》,对于泸沟桥的印象来源于影像残缺的资料,汪建伟按照自己印象的顺序排列出来,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视觉档案。
《事件》是汪建伟1992年的一件作品,那时他的野心是想颠覆整个视觉系统,这件的作品只有一叠很厚的手稿。当时策展人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把许多领域的人都招集到日本开会,包括库哈斯(Rem Koolhaas)等人,谈学科界限与文化领域的问题,会议整个画册用的是汪建伟的 二页作品作为封面。汪建伟的这件作品不似其它艺术家递交的方案,上面根本没有图片,全是由数字组成,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系统。
1993年10月,汪建伟在四川和农民共同种植了一亩小麦,相约共种一季度,期间观察与记录种植动态综合系统,表明信息在一个更广泛的输出输入系统中 的循环本质,这件名为《循环》的作品是没有具体形态的观念化的行为作品,它把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产、农民作为社会学定位的身份和艺术家的身份这三个意义 的东西放在一个空间完成,作品曾在荷兰以幻灯片与文献资料的形式放映过。
《生产》是1996年汪建伟跑到四川去了六个县城拍了8个不同茶馆的人的日常生活,作品把艺术家“生产”的现场与公众的“生产”的现场完全重叠在一 起。汪建伟考虑一个公共话语在今天还能不能支配人的话语,并反复调查是什么样的公共关系建立了这样一个空间。从文本的角度看,茶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和私人 空间在这样一个场所怎样构成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侵略性。实际上它也就是研究我们是怎样过日常生活的。如果说“种植循环”计划仍然还看得见要寻找一种艺 术、农民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关系,“生产”的界限在这里已经完全不是线性的了,而是重叠的。当时汪建伟的阅读背景已经从福柯(Michel Foucault)直接到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布尔迪厄研究的是空间的意义、习性、话语这三种关系建立起来日常生活状态与意义,恰好是这方面专家的卡特琳娜?戴维当时看到这部作品 后,邀请汪建伟参加了1997年的文献展。
多媒体与剧场的结合
汪建伟是国内最早把多媒体与剧场进行重叠,将影像、音乐、灯光等多媒体艺术和剧场里演员的表演融为一体的艺术家。艺术家对于社会是会有反映的,并跟这个社会产生关系,而作为艺术家的汪建伟总在不停地发现有可能性存在的空间与方式,他走到这步是必然的。
2000年的时候他开始有了《屏风》这部作品,它表达的是在公共场所的一种行为规范的“屏风”的心理观念,也就是哪些东西是公开的,那些东西是遮挡的,这个界限有时候很难找到确实在什么地方,它又在不断的游动。作品呈现出双重目光重叠在一个空间里的共时性空间。
《仪式》是第二个作品,这部作品受到了法国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即文献、知识、话语的关联性,以三个不同的‘击鼓骂曹’文本为依据,对事件的历史真实和文本真实进行了综合的演绎,将故事的文本历史和艺术家对它们的思考与分析一并呈现。
去年广州三年展作品《景象》是汪建伟把剧场里的人已经抽离,将被仿自然风吹动的塑料袋本身作为一个戏剧的主角,这个风是不自然与间歇性的,并不能形成 一个方向,几千个塑料袋飘得特别象个剧场。在考虑这个作品时,汪建伟把其中的视觉部分也去掉了,原来的方案是有部电视在播放里面有黑旗在飘的内容,但他觉 得太好看太视觉了所以放弃了,并且他想使作品故意保持一种很廉价的感觉。这种不确定、偶发性的空间形成暧昧的关系,艺术家称之为“景观”。
目前正在展出的《飞鸟不动》里现场的人被换成了三个连续时间片断的雕塑,展厅的灯光非常讲究,在光与影的灰色地带呈现出剧场的概念。作品里汪建伟把雕 塑的时间概念拉长了,这个概念还将体现在他5月20号在上海沪申画廊的个展里。对于飞鸟不动的录像部分演员的控制,汪建伟希望演员把自己的理解加入作品 里,让他们保持个体与表达他们自身某种能力的“参与者”的状态。“参与”在整个关系中能够始终保持“在场”,使现场有一种此时此刻的意义。这个准则也具体 体现在他以前的多媒体戏剧作品里对于演员的要求。
空间的关系、共享、重叠
对于现场艺术,它有很多关系,有时候它是在一种联接点上,汪建伟认为谈原创不如谈关系,如同发明,其实是在若干个关系点上,别人要了解发明还是要了解 那些关系,所以艺术家不如回到关系上。剧场里这种关系表现在布景与装置的概念是重叠的,表演与行为是重叠的,这个关系是汪建伟直接从建筑上吸取的,叫做重 叠空间,它是由两部分因素共享一个关系。视觉经验的很多方法也是一种关系,在关系中去构建与阐述,不是替代和罗列。在作品里,艺术家故意消除视觉状态的延 续性,重叠的空间则是要建立一个矛盾的空间。
《蜘蛛》作品里探讨的也是生物行为与建筑共享的概念,蜘蛛进入别人空间并且占有空间做的自己生态建筑,但是并没有伤害其它人的空间。人类如果真要去征 服某个关系,是要看相互共享之间能否达到一个平衡。汪建伟的对于空间的概念还直接体现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里跟开幕式是 重叠的,它是对人的直接介入。作品提供了一种同质、异质、混合的文化生态景观。
汪建伟策划的《间·隔》展,也是他的一个作品。它关心的是对隐性的空间察觉,在他的策展文字里写道“我们不同意任何现存关系的合理性,但以坚持对它的 合法性的态度去给予现场这个空间以新的维度与更多的可能性。有序与无序的界线在这里变得非常不可靠,当我们在熟悉的秩序中变得生涩与茫然,就有可能为可能 性的世界作好准备。间隔过渡的两端是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对空间内部的处理不是受到某种理论诱惑的流露或当代艺术程序化操练,而是在谈论一个沉默的关联与关系。”
|